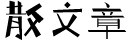具象诗的起源
“除了星座(CONSTELLATION★)之外,沒有什么会发生吧。”
在最早发表的新诗运动指导手册《从线型到星座》中,瑞士诗人贡林格(Eu.gen Gomringer)一开头便引用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这句话。这本手册出版于1954年,他的诗集《星座》(Konstellationen) 前一年已由伯恩的端旋出版社(Spiral Press)印行,在文学界、造型艺术、音乐、设计等各领域的前卫艺术家之间,激起了相当大的涟漪。
这本诗集正如书名所示,辞汇从原本线型的诗的形式和文法结构中解放,每一个用语都像星座一样被配置在空白的空间里,同时唤起相互之间的共鸣,就像语汇的结晶体,形成新的诗体。这就是被称为“具象诗”(concrete poetry)的起源之一。
“具象诗”的发源地是德国乌尔姆(Ulm)。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承包豪斯运动理念而成立的乌尔姆造型学院,日本的设计史已深入介绍该处的设计运
就及其革新性的历史背景,因而广为所知,但似乎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同时也是“具象诗”的发源地。
乌尔姆造型学院的草创期是在1953年前后,大学的共同创立者、也是第一任校长的比尔(Max BilI),以及亚伯斯(Josef Albers)、冯登伯格-吉尔德瓦特[Friedrich Vordemberge-Gildewart)、阿根廷的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等具体艺术(concrete art)的艺术家,以贡林格为首的海森布特(Helmut Heissenbüttel)、安森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等诗人,和以信息理论为基础、提侣前卫关学的本泽(Max Bense)等人,都参与乌尔姆草创时期的计划,让乌尔姆成为国内外前卫艺术家和理论家蓬勃交流之地,也是艺术、设计和知识变革发生的第一现场。
贡林格提出的“具象诗”这一种新诗体也是在乌尔姆这样的环境下誕生的。当然,这个具象诗的概念和后来比尔推动的“具象艺术”有着连带的关系。1955年,皮纳塔里(Décio Pignatari)到乌尔姆拜访具体主义者比尔和“星座”诗人贡林格;皮纳塔里先前与德坎波斯兄弟(Augusto & Haroldo de Cam=pos)一起成立巴西的新诗运动文学团体诺伊甘德雷斯小组(Noigandres
group)(1952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乌尔姆的文艺活动国际化的一面,这也成为而林格和诺伊甘德雷斯小组共同提倡“具象诗”文学概念及新诗运动的契机。其实这股将诗和语言视觉化、空间化的全新尝试,于20世纪50年代已经在世界各地同时蕴酿进行着,故当贡林格和诺伊甘德雷斯小组共同提出“具象诗”的称呼和理念时,才能立刻引爆成为跨国际的运动,也成为起越20世纪60年代各艺术的分界,激发各领域互相渗透的创造力之导火线。
马拉美的“星座”和具象诗之“星座”原理
我在乌尔姆留学时,开始亲身接触比尔以和“抽象”相对的“具象”概念为基础创作的绘画、雕刻、印刷图案、产品设计,与延仲到建筑等广义的造型活动,还有贡林格的诗集《星座》,那年刚好是皮纳塔里访问乌尔姆的第二年。这个体验成为我往后选择工业设计和设计学专业,至今投入具象诗的创作和参加国际活动的契机,同时也是我重新思考西洋近代文明的意义或是西洋近代艺术革命的基本精神层面的重要契机。
贡林格将诗集取名《星座》是受到马拉美的彩响,其意象的背后,正是警打20世纪前西洋诗传统的线型诗体概念,实现马拉美将字词像星一般排列的理念——“般子一掷断然拼除了偶然”,这句话出自马拉美的《数子一想(1897年)诗来书封。
翻开这本诗菜,每二页形成一个画面,各种语句以七种大小不同的字体,像至座靓配置在白色的书页上,连成一片的书页就像在观看星空般。各语句和背器延伸的空白空间相呼应,嗅起并结合与词语相关的各种知觉,创造形象、声音和意义的多重波动,让不存在的世界在书中显现,成为一卷宇宙生成的延展解蒂。就像后来所说的,这种新的表现方式跨越了世纪,在近代的艺术革命上,语言或文字也能离开书页和诗的线型传统,在空间中尽情舞出许多的可能性。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具象诗”也明显继承了马拉美以降,“语言本身即为主题”这样崭新的诗的精神,更加重视文字语言的空间作用、语言的图像性、多元意象的召唤力。但是,20世纪50年代这股诗论的动向,另一方面也加入了同时代的语言学、分析哲学、信息理论、记号学或信息关学和具象艺术的“具象”(concrete)思想,形成方法论,强化其理性的发展,像是语言素材
或记号本身的自律“关系”或是“结构”(structure)的呈现,可以说,语言更加趋于物质性和客体性。
例如,具象诗在初期可以举出以下几个主要的基本原理。像是重视案材和结构要素形成的视觉性和视觉空间的价值,基本单位的组合,以星座般的共时性配置取代线性的内文排列,空间中多重焦点的知觉和时间性,脱离语言意义唤起的多重意义和泛义性,不光只是传送信息、表现情感,更要传达出结构,结构的瞬间传达性,重视表意文字的构想,语言作为一种素材的音声元素、形态元素、意义元素——这些元素同时存在着,反主观、反隐喻的语言实现,文学的国际化、超越国家性等等。
从这样的理念就能得知,具象诗虽然以拥有“意义”的语言为素材,同时也和具象艺术相通,不是只去模仿和描写“某种事物”,而是以一种自律成形的诗,构思之后然后具象化。在这样的意义上,具象诗不光只是从线性的语言朝向图形化、空间化发展,更进一步来说,更接近一幅构成的绘画,或是极接近图像般的东西。这在重视语言的表现面,尤其是文字形态的视觉性层面上,乍看或许和印刷图案设计有着相似性。之后加入照片或拼贴等素材,成为视觉性更强
的视觉诗,这样的发展成果和广义的图像(graphic)究竟有什么不同,几平难以判定。
近代艺术革命的意义--语言的活动化,消型的治再化——各科感激的两线合
但是,就如马拉美所预言的,重新去回想20世纪初艺术革命的特点,语言的视觉化、空问化、图像化可说是20世纪艺术新冒险底层共同的特征。例如,从摩根斯坦(Morgenstem)的绘画诗、阿波里奈尔(Apollinaire)的宇画诗(calligrammes)、马利内提(Marinetti)的未来派自由诗,到达达和风格派(De Stjil)为主的中欧及俄罗斯构成派的形象诗等,诗和语言各式各样的图像化、造型化尝试,可说是随处可见。
这一种近代艺术的特征不仅如此,类似于诗或语言圈像化、造型化的现象,也出现在和语言的规范性相近的音乐记谱法,从音符的记谱转变成以图形乐谱的音乐图像来记谱(作曲)的尝试,可说是在同一个趋势之下。此外,立体派19
很早就把报纸印刷内文的片断和文字当成素材加入画面,像超现实(cubism) 主义和达达主义,
有时甚至将语言当成素材加入画布,以呈现绘画更多不同的
样貌,可以说是将绘画带往语言化之路,这也是20世纪艺术的另一个特征本画期语言方向靠拢的同时,画面构图不单只是追求颜鱼和形状的图像要套,和文字及内容的语言要素两者之间具有同时性,造型本身更需要综合各种感觉,这样一种新的语言表现成为创作者的憧憬和追求目标。
例如,康定斯基(Kantinsky)提出了“形态语言”和“色彩语言”的概念,把形态和色彩当成一种“语言”来看待,或是在谈论圆为蓝、四方为红、三角为黄这种造型和色彩的共鸣作用时,他正是以语言为目标,或说是以音乐为方向。此外,在讨论“点、线、面”时,他追求一种“造型语言”,也就是新的语言的构成文法,或是像对位法般的作曲方法,可以明白看出他试图做这样的建构。克利(Paul Kiee)也同样在做这样的尝试。克利的重要著作《造型思考》也同样明白地指出他对“造型”上的语言构成文法或是作曲法的探究。基于语言的思考,换句话说,也就是基于逻辑的思考,发展出西洋的近代文明。在这层意义上,西洋的思考可以说是语言本身。
也因此,克利提出的“造型思考”,其概念本身就有老革命意义。这样的“造型思考”应该包含了以下的意义吧;其一是,把造型当成一种新的语言来建物其构成文法;另一个是所谓的“语言也包含在内”,“借由意象的思考”取代语言思考,这种最原始的思考将在新的面向之中诞生。换言之,和康定斯基一样,克利也致力于将近代被分割的众多感觉再综合与整合,希望建构一个新的语言字宙。
包豪斯从康定斯基及克利身上学习,并称呼这二人是自己“艺术的父亲”,“具象艺术”的推动者比尔则认为自己在造型上还有“更多的父亲”。其中的主要人物,举例来说,有风格派的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杜斯伯格外,还有雕刻家范东杰洛 (Georges Vantongerloo)。
放弃模仿自然、朝“抽象”迈进的20世纪艺术运动,在原理层面的极限中,谊求更纯粹且严格的抽象构成,即是风格派。造型要素被还原成垂直、水平、倾斜的直线,和三原色、无彩色,这也可以说是追求自律的造型之语言化。语言被认为是由“差异”或是“对立”形成的,这种语言化的追求,宛如是追求语言的内在关系之结构。
什么呢?被还原到极限的几何学造型要素和基本色彩,是自然内在方质上的对立要素。对他们来说,追求这种对立关系的极致之均衡是新时代持神告象乐,他们借由这些象征来否定超越自然的近代自我,试图唤起人类也包含在其的宇宙精神均衡和调和的意象。
具象艺术的“结构”——图的活画商生出意意最前生
实上,“具象艺术”的“具象”(concrete)之名,是1930年时风格派创始人杜斯伯格所提倡的概念。他主张以色彩和形态等造型手段取代模仿自然,将育律的视觉概念加以具象化,这样的绘画造型不该算是“拍象”,而应该称为“具象”。这和蒙德里安的思考如出一辙。之后,康定斯基也提出新的“艺术的世界”应该和“自然的世界”并肩而立;他并且以为,由色彩和形态组成的“抽象艺术”的世界,也应该和实际存在、具象的“自然”一样,是另一个真实的世界,具象的世界。因此,所谓的“抽象”艺术应将之命名为“具象艺术”才对。
继承这个以“具象”来取代“抽象”的讨论,之后并将“具象艺术”扩大成为国际运动是比尔之功。他在1947年检讨了本世纪里许多艺术新概念的意义。像是“非客体”、“抽象的”、“抽象化”、“抽象艺术”、“具象”、“具象化”等等,以“具象艺术是将抽象的思考本身,以纯粹的艺术方法化为可视的艺术”为真体艺术下了首个精确的定义。
但是,这个“具象”的概念,因为和杜斯伯格及风格派的印象有所关连,很容易被认为等同于几何学的构成主义,引起许多人的反感,故20世纪50年代时,比尔导入了“结构”概念,让“具象”的特质更为广范而丰富。比尔导入“结构”的概念时,可以推论他一方面将以集合论为基础,企图重新建构布尔巴基(Nicolas Bourbaki)派的数学“结构”列入考虑,另一方面也将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原点、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等人结构语言学中的“结构”思考进去。后者和李维史陀(Lévi-Strauss)之“结构”概念相关的观点,也和以哥特形态学出发的天文学家茨威基(Tsuviky)的形态学结构观有所交集。比尔在1956年发表的重要设计理论“形态学的方法而形成的环境”中,就是以茨威基为出发点。
而目,这里的“结构”,指的是本泽以现代宇宙观为根基的信息美学,由此加以扩展的理论。其美学无法以绘画、雕刻、设计、诗、文本等对象物的分类来掌握,只能像是印刷的网点和电视的点线原理,色块、形态元素、文字元素等等,以物质分布的状态或过程来掌握。
有了上述同时代的世界认知观点后,其“结构”的概念才能成立,从结晶体般的几何学结构,发展到混沌的无定形(amorphous)的形象;即从宇宙(cos-mos)到混乱 (chaos),全都包含在内的字宝论才有可能成形。因此,这个“结构”概念可以说是结合了现代的数学宇宙观和哥特形态学的宇宙观。也可以说是将结构用一种新的“图”的语言形成的形态学思考,或是形象思考的再生。换句话说,“借由意象的思考”,也是意象思考的再生。
另一个“结构”——星应思考之要现
我们已在之前谈过,这个“结构”的概念也是“具象诗”的主要创作原理。就像在马拉美和贡林格的诗学中看到的,意味着“星座”的“constellation”可
以说是这个“结构”概念的新臂喻。“星座”正具有唤起空间配置和关联性的多样网络,以及如银河星系般分布的形象结构,同时也是知觉的意象结合了神话的宇宙图像。
但是,这个“constellation”不只是单纯的“星座”的“结构”高意,也是西欧的近代艺术放弃模仿自然,破坏传统艺术语言,在彼方发现了新的时间和空间的象征概念。这是取代存在与存在之间的空白,或是负(minus/negi-tive)的意义、多焦点性、图像和实体世界的等价值性、非对称性、同时性、取代个体性和客体性的物质结构和组织等的价值发现。空白和负、多焦点性、图像和实体世界的等价值性等,就像另外的记号般,也可以说是空间“相互渗透性”和“透明性”的发现。
原来,“星座”或“星系”可说是用以比喻这种特质最恰当的结构。因此,“constellation”不光是新的诗之形成原理,也是近代艺术全体共同的新的思考原理。所以,构造这种新的“图”的语言,一方面是“星座”,也是发现星座式的思考,由星座而来的意象思考的再生。
在具象艺术或是具象诗的领域里,依据结构语言学提出的诗的语言“美的机
能”,与本泽“美的信息”之形成,取代了单纯的意义传达或是沟通机能,或为具有艺术精神的新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本泽的信息美学之提点斯图加特。成为许多诗人、造型艺术家、建筑家、音乐家、设计师等跨领域蓬勃交流的地点,也是具象诗的实验和新媒体、首次出现电脑艺术理论和实践的国际交流场所。
问题的发展或许有些迂回,西洋近代艺术的革命如上所述,造型语言化、语言被当成造型来掌握,为了在新的面向将混合了各种感觉机能的原始意象思考还原,而进行各式各样的精神冒险。
莫霍伊-纳吉(Moholy-Nagy)在其著作《移动中的视野》(Vision in Motion 1947年)中,全面地检讨20世纪造型语言的哲学和方法论,除了美术、摄影和电影领域外,更跨越到舞蹈、音乐、文学、诗的领域。这本书的意图正是尝试将造型当成一种语言,把语言当成造型来重新掌握,探寻能再综合人类丰富的多种感觉机能之道,重新审视新的个体和社群的位置,这些重要的尝试,在本文中再次一并提出。
另一方面,西欧近代的新诗运动中,“具象诗”的构想虽然古老,却依然有着新的理论观点。当马拉美发表“将语言如早座般地配置”的诗作,另一位诗人的诗学也支持相同的观点。1897年到20世纪初,在日本停留了许多次学习“汉字”,在汉字中发现映照着自然事物和变迁过程,并深深受到感动,写下了诗论《诗的媒体汉字考》的西洋诗人就是费诸罗萨(Ernest Fenollosa)。这本《汉字考》中,费诺罗萨比较了汉字和西洋语言线形声音记号的表记法,在汉字的表意性中发现原始的语言能量,把汉字以“思想绘画”、“动作语言”来看待,并发展出震憾人心的直觉观和富洞察的诗论。
这本诗论是费诺罗萨的遗稿,由诗人庞德(Ezra Pound)编辑出版,才首度广为流传。庞德经由这个编辑工作,继承了费诺罗萨身为诗人的直觉和洞察,认为汉字具有创造新诗的活力泉源,可以唤起具体的意象,提倡所谓的“意象主义”(imagism)的诗学,对英美和意大利、法国等的新诗运动有不小的影响。而且,这本《汉字考》对现代的具象诗和视觉诗的推动者也有极大的影响,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德语译本则出自贡林格之手。
现代知识的冒险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说过,费诺罗萨的诗学和店拉美的星座概念,两者正“动摇了西欧以逻辑为主的形而上学和诗学的程本,让最根本的西欧传统开始崩毁。”
费诺罗萨的诗论中,除了指出音声记号的西欧语言强化了其线形特性,“为了达到迅速传达的目的,让语言的贫血症越来越严重”,并强烈指责其逻辑的线形特质和工具性;相反地,他认为汉字吸收了自然的诗的本质,现在更强烈地散发着其意义的“光环”。以现代的角度来看,.费诺罗萨对汉字的异常热情,可以经易看出仅有二十几个字母、表音记号的西欧语言在面对近代时的精神状况。
即使如此,从19世纪到20世纪,推动近代知识变革的先驱,竟是将语言视为媒介的诗人,和把诗当成艺术原点的作家,这件事真是意味深长。因为诗的语言和图像,或是图像的意象和宇宙观、韵律形象、歌谣、舞蹈等等,重新唤起了其和宇宙最原始的关系。另一方面,语言的图像回归,也可以说是中世纪祈求在曼陀罗的图像中获得新的思考,同时也是安德鲁·拉洛伊-鲁汉(AndreLeroi-Gourhas)在《动作和语言》中提到,“神话文字”的诗的语言之新建设,1960年代到1970年代,“具象=视觉诗”成为前卫艺术概念变革的里程碑,正是因为具象诗的语言具有唤起超越领域的意象之力量。
皮尔斯的符号学和具象诗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世界从混乱到建立了宇由观,从无秩序到有秩序,这样的宇宙进化观念和人的思考过程的根本重叠,产生种种语言的、非语言的记号,例如,敲门的声音、足迹、叫声、动作、绘画和乐谱、表意文字、会话、沉默的冥想、三段论法、代数的等式、几何学图形、宇宙图、风向球等等。为了重新综合所有记号而诞生的语言学“符号学”(semlotics),产生了一位一生贡献其壮大构想和建设的惊人思想家,他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始祖,皮尔斯(Charles S.Peirce,1839~1914)。
皮尔斯的主要著作出版于1940年代,已是他死后的二十多年,其中也有离执笔时间已超过一世纪的内容,其著作的刊行刚好让欧美的前卫诗人,特别是具体诗的先锋者感到鼓舞振奋。皮尔斯记号的类别分成图案(icon)、索引(in-dex)、象征(symbol)到图像(image)、图表(diagram)、隐喻(metaphor)等等,其中语言及非语言的记号同时包含在内,这一点着实令人着迷,让具象诗及视觉诗的诗人们更加沉醉的是关于实存的图像论等表意文字论。
不只如此,皮尔斯在抄写爱伦·坡的《大乌鸦》诗时,字体和独特的韵律产生
共吗,有时甚至和下一行的线型诗有着共鸣,开创出一种字体般的文字空间把语言因诗的机能而产生变化音和意义的结合,转换成文字和意义的视觉交互作用,可说是一种实验性的新尝试。这样的尝试之中,语言的发生也和音色、形、空间、时间、韵律、运动等人类的各种感觉混合,原始的生命记忆不正是这样形成的吗?这样的感觉重新被唤起。
超越“汉字”的象形性、图像性——从世界的生命基础到点言形或
在日本,最早和具象诗的国际运动交流者,是与庞德有深厚交情的北园克卫和他的团体“VOU”。但是,北园在和具象诗运动保持一段距离之后,就因“起自鹅毛的诗的历史在圆珠笔手中就应该结束了”这一段话的刺激,开始发展造型诗(plastic poem),并转向“相机的滤镜中,由揉成一团的纸屑,牛皮纸或是玻璃的碎裂演出的诗”这种影像诗的方向,将诗的形成解放到更为近代文明的广大层面中,形成一个独立的诗的宇宙。
和国际运动的合作方面,积极推动具象诗的倒不如说是1964年以后(1977年
为止】新国诚一主办的“ASA”运动。他和在具象诗中提倡空间主义(Spa-tial-isme)的法国诗人加涅尔夫妇(llse & Pierre Gamier)有很深的交流,并且参与日文和法文的共同创作等工作,把自己定位在“空间主义/具象诗”上。新国诚一和北园克卫正好相反,他否定照片等其他素材共同存在的混合艺术,始终守护着语言本身就是客体的理念。新国借汉宁再表意化创造出的美丽新图像,可以说是语言结晶组成的诗的宇宙。
“具象=视觉诗”的西洋作家和研究者,至今依然对日本的书体,尤其是汉字的意文字具有的“图性”或是“图像性”十分关注,对于日本的“具象=视觉诗”评价也极高,但是日本诗人们却没有因此对汉字的象形性和图像性产生特殊的依赖,反而想要跳脱自己的语言,重新建构一种新的语言。
即使如此,在西欧眼中,汉字的“图性”或是“图像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推论,即汉字不单只是具有象形性,汉字诞生发展时所拥有的图像般的空间布置特性,这种“constellation”、图的特性中隐含着“什么”,不是吗?首先,汉字构成的多样性,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constella-tion”吧。本雅明在“原始的存在布置”其类别提出了“星座/配置”(ko
tellation)的概念,这个“星座”也拥有唤起汉字的原始意义之象征性吧。费送罗萨从汉字感受到的“意义的光环”,不光只是其象形性本身,更是超越其象形性,根植于宇宙生成的汉字生命形成的原理,正散发着“星座”的光辉吧.西欧在近代史上一路解构传统,其所要追求的,就是这种原始生命的语言之形成原理,也就是这个“星座”再生的理念吧。今天,即便是“汉字”也好,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其象形性和图像性,回到原始的诞生之处,再次去面对世界生命的基层之处生成的语言。